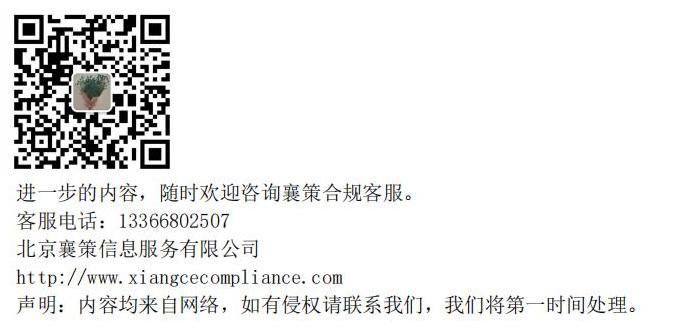家族信托:神器与暗器的边界 —— 从许、宗案例看设计
录入编辑:襄策合规 | 发布时间:2025-10-11家族信托,这一源自英美法系的财富管理工具,在我国历经数十年发展,已成为高净值家族守护资产、传承家业的重要选项。但 2025 年以来,两起备受瞩目的司法事件撕开了工具背后的核心逻辑:许家印夫妇在美国设立的 163.8 亿元家族信托,因 “控制权过度保留” 被香港高等法院通过 “沙布拉禁令” 部分击穿;宗馥莉卷入的 18 亿美元离岸资产争议,因信托设立证据模糊陷入继承纠纷。同样的工具,却呈现出 “避险失效” 与 “传承遇阻” 两种结局。
对高净值人群而言,家族信托绝非 “资产打包放入即可高枕无忧” 的保险箱,而是一套需精密规划的法律与财务综合方案。若设计失当,不仅无法实现财富传承、风险隔离的初衷,反而可能成为债务追偿的 “靶点” 或家族内斗的 “导火索”,从避险神器异化为伤己暗器。本文将结合上述典型案例,从信托目的锚定与设立地选择两大核心维度,拆解家族信托的整体设计要点。
一、案例透视:两种信托实践的警示与反思
(一)许家印海外信托:163.8 亿元架构被击穿的核心症结
据香港高等法院 2025 年 10 月《HCCW 123/2025 号判决》及公开信息,许家印夫妇于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3 月间,通过两家 BVI 壳公司在美国特拉华州设立单一家庭全权信托,将 23 亿美元(折合人民币 163.8 亿元)资产纳入其中 —— 资金源自恒大上市后夫妇二人分得的 500 余亿元股息分红,受益人指定为两名儿子,表面目的直指 “财富传承与债务隔离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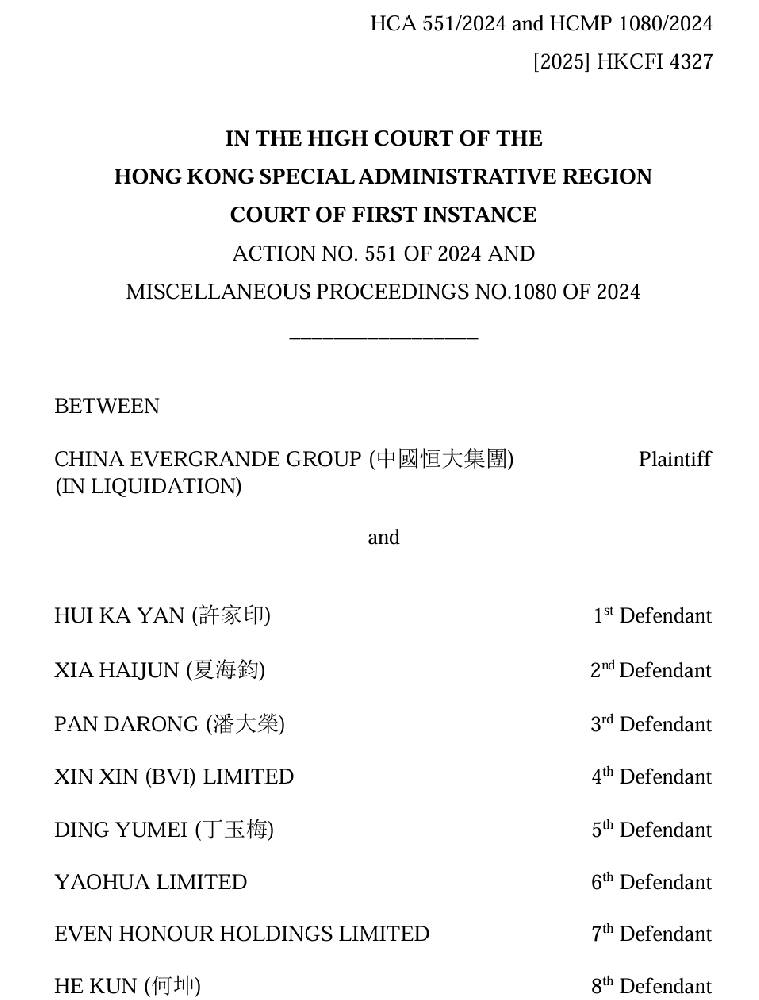
然而,当中国恒大清盘人以 “信托资产未实质独立” 为由申请冻结后,香港高等法院最终裁定行使 “沙布拉禁令”(跨境资产冻结令),导致信托的风险隔离功能部分失效,资产被纳入可执行范围。法院穿透架构的关键依据在于 **“控制权实质保留”**,这一细节恰恰戳中了财产保护类信托的核心禁忌:
1. 突破全权信托的规则底线:虽名义上由美国专业机构担任受托人,但证据显示,许家印通过私人助理向受托人发送17 份 “投资建议函”,指令将 8 亿美元投入恒大关联企业,且在债务危机爆发后直接要求受托人划转 3.2 亿美元至指定账户用于偿债。这种 “建议即指令” 的操作,彻底架空了受托人的独立决策权,使信托资产与委托人自有资产形成混同。
2. 设立目的涉嫌规避债务:信托核心资产注入期(2019-2020 年),正是恒大有息负债突破 8000 亿元、首次出现商票逾期的债务风险敏感期。更关键的是,信托文件中暗藏 “危机触发条款”—— 约定若委托人出现债务违约,受托人需 15 日内将资产转移至关联方控制的离岸账户,这一设计被法官认定为 “具有隐藏资产、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”。
(二)宗馥莉信托争议:18 亿美元资产归属的 “信任危机”
与许家印信托的 “主动失控” 不同,宗馥莉卷入的信托纠纷,暴露了家族信托设计中 “证据缺失” 的致命风险。2024 年 12 月,宗氏三兄妹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宗馥莉,主张宗庆后生前在香港设立离岸信托,将离岸公司建昊企业名下 18 亿美元汇丰银行资金纳入信托财产,且承诺每名子女可获 7 亿美元利益。
截至 2025 年 9 月,该案历经三次庭审,香港高等法院先后颁布临时禁制令与资产冻结令,虽暂未对信托效力作出最终判决,但核心争议已清晰凸显信托设计的关键漏洞:
• 信托成立的 “三确定性” 缺失:原告仅能提供《初步信托协议》扫描件及提及 “子女利益分配” 的《沟通纪要》,无法出具经律师见证的原件,且未明确约定信托财产范围(18 亿美元是否全部为信托资产)、分配比例等核心条款,不符合香港《信托法》对信托成立的基本要求。
• 财产属性的举证困境:原告以账户标注 “Trust Account” 主张为信托资产,但宗馥莉方面提交了该账户用于支付东南亚供应商货款的凭证,辩称资金实为集团营运资金,双方各执一词却均缺乏决定性证据。
• 口头承诺的法律效力空白:三兄妹所称 “宗庆后口头承诺利益分配”,因无书面记录未被法院采信,成为纠纷升级的重要诱因。
二、设计核心一:明确信托目的 —— 在 “控制权” 与 “隔离性” 间精准取舍
“谋定而后动” 是家族信托设计的首要原则。许与宗莉相关案例的教训表明,信托目的模糊或功能错配,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结局。
(一)信托功能的三大分类与适配场景
历经 6 个世纪发展,英美法系已形成成熟的信托功能体系,为我国家族信托设计提供参考框架,三类核心类型需精准匹配需求:
1. 财产保护类信托:如全权信托、特拉华信托,核心目标是隔离委托人债务风险,确保资产稳定传承。此类信托的生命线在于 “资产独立性”,要求委托人彻底放弃控制权 —— 不得干预投资决策、不得指令资金流向,否则极易像许家印信托一样被法院穿透。适配场景:高负债企业主、高风险行业从业者的风险隔离需求。
2. 控制权保留类信托:如 BVI VISTA 信托、私人信托公司(PTC)信托,核心目标是在传承资产的同时保留企业控制权。此类信托允许通过指定家族主导的 PTC 担任受托人、设定投票权规则等方式实现控制权平衡,但需在条款中明确权力边界。适配场景:家族企业二代接班、需维持控制权稳定的传承规划。
3. 税务筹划类信托:如委托人年金信托,核心目标是降低遗产税、赠与税等税负。由于我国尚未开征相关税种,国内更多是在上述两类信托中附带税务优化功能,而非单独设立。
(二)核心矛盾:财产保护与控制权保留的 “鱼熊之辩”
许信托的悲剧,本质是试图 “既要又要” 的逻辑陷阱 —— 既想通过全权信托实现债务隔离,又不愿放弃资产控制权。从实务来看,两者的排斥关系无法调和:
• 若以债务隔离为首要目标,必须斩断委托人对信托资产的 “任何实质影响”,包括避免关联方担任受托人、不设置 “可干预条款”、确保资金来源与企业经营无直接关联。
• 若以控制权稳定为首要目标,需主动放弃 “绝对隔离” 的期待,通过 BVI VISTA 信托等特殊架构明确控制权边界,例如约定 “委托人仅保留股权投票权,收益权由受益人享有”,避免因过度控制丧失信托独立性。
三、设计核心二:选择适宜的设立地 —— 法律环境决定信托 “生命力”
信托设立地不仅决定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地,更直接影响信托效力的跨境认可度。许家印选择美国设立信托、宗氏三兄妹在香港起诉,均凸显了设立地选择的关键作用。
(一)设立地选择的 “两步判断法”
结合襄策实务经验,委托人可通过 “两步法” 平衡便利性与合规性:
第一步:按财产分布 “就近匹配”
◦ 境内财产为主:优先选择境内设立。我国《信托法》虽对民事信托规定较原则,但境内房产、国内企业股权等资产纳入境内信托,可减少外汇备案、跨境税务等操作成本,且避免法律冲突风险。
◦ 境外财产为主:若持有 BVI / 开曼公司股权、海外账户资金等,可在资产所在地或信托法律成熟的离岸地设立。例如许将美元资产纳入美国信托,符合 “财产与设立地匹配” 原则,但未充分评估香港法院对美国信托的认可尺度。
第二步:按功能需求 “制度适配”
◦ 境内信托:优势在于监管透明、沟通便利,但信托财产类型受限(如未上市股权纳入难度大),功能较单一,适合简单的资金传承规划。
◦ 离岸信托:BVI、开曼、香港、新加坡等地区法律体系完善,功能灵活 ——BVI VISTA 信托支持控制权保留,香港信托与内地司法衔接更顺畅。但需警惕 “法律孤岛” 风险,如张兰在库克群岛设立的信托,因新加坡法院不认可当地对债权人的严苛举证要求而被击穿。
(二)关键风险:设立地法律的 “国际兼容性”
离岸设立地选择不能仅看 “对委托人的保护力度”,更需评估法律的国际认可度:
• 香港、新加坡等地区的信托法律虽对委托人权利有所限制,但与普通法体系高度兼容,其信托效力在跨境争议中更易被认可,适合有跨境资产配置需求的家族。
• 部分离岸岛国虽制定了对委托人过度有利的规则(如缩短债权人追索时效),但可能不被其他国家法院承认,最终导致信托沦为 “纸上协议”。
四、结语:信托设计的本质是 “规则敬畏下的精准匹配”
从许信托被穿透 163.8 亿元资产,到宗卷入 18 亿美元继承纠纷,两起案例共同印证:家族信托既非 “包治百病的神器”,也非 “必然踩雷的暗器”,其效力取决于 “需求与设计的匹配度” 及 “对规则的敬畏心”。
对委托人而言,搭建信托前需做好三项核心准备:
1. 需求厘清:通过与律师、财务顾问深度沟通,明确是 “风险隔离优先” 还是 “控制权保留优先”,避免 “既要又要” 的认知误区;
2. 法律尽调:对设立地法律、信托类型进行全面评估,例如选择美国信托需预判香港法院的裁判倾向,设立香港信托需确保条款符合 “三确定性” 要求;
3. 证据留存:信托协议需签署原件并经律师见证,明确财产范围、分配规则等核心条款,避免依赖口头承诺,同时妥善保管资金流向凭证、沟通记录等辅助证据。
家族信托的价值,在于为家族财富搭建 “稳定的传承框架”,而这一框架的基石从来不是 “规避规则的技巧”,而是 “遵循逻辑的精准设计”。唯有明确目的、选对土壤、细化规则,才能让信托真正成为守护家族基业的 “神器”。